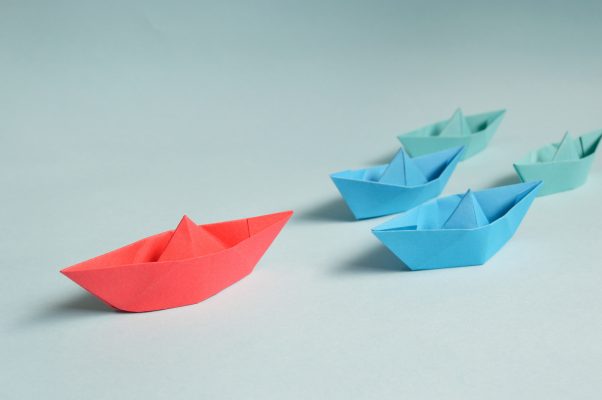心靈勵志
「好了傷疤忘了疼」——健忘,原來是讓心靈得到救贖的解方。
文/周國平
人得救靠本能
習慣、疲倦、遺忘、生活瑣事……,苦難有許多貌不驚人的救星。
人得救不是靠哲學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類和個人歷盡劫難而免於毀滅,各種哲學和宗教的安慰也無非是人類生存本能的自勉罷了。
人都是得過且過,事到臨頭才真急。
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來,只要不死,好了傷疤又忘了疼。最拗不過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產生的日常生活瑣事,正是這些瑣事,分散了人對苦難的注意,使苦難者得以休養生息,走出淚谷。
在《戰爭與和平》中,娜塔莎一邊守護著彌留之際的安德烈,一邊在編一隻襪子。
她愛安德烈勝於世上的一切,但她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麼事也不做。一事不做地等一個注定的災難發生,這種等待實在荒謬,與之相比,災難本身反倒顯得比較好忍受一些了。
只要生存本能猶在,人在任何處境中都能為自己編織希望,哪怕是極可憐的希望。
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終身苦役犯,服刑初期被鐵鏈拴在牆上,可他們照樣有他們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別的苦役犯一樣,被允許離開這堵牆,戴著腳鐐走動。如果沒有任何希望,沒有人能夠活下去。即使是最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們的徹底也僅是理論上的。
在現實生活中,生存本能仍然驅使他們不斷受到小小希望的鼓舞,從而能忍受這遭到他們否定的人生。
請不要責備「好了傷疤忘了疼」
如果生命沒有這樣的自衛本能,人如何還能正常地生活,世上還怎會有健康、勇敢和幸福?
古往今來,天災人禍,留下過多少傷疤,如果一一記住它們的疼痛,人類早就失去了生存的興趣和勇氣。人類是在忘卻中前進的。
對於一切悲慘的事情,包括我們自己的死,我們始終是既適應又不適應,有時悲觀有時達觀,時而清醒時而麻木,直到最後都是如此。說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適應力是驚人的,幾乎能夠在任何境遇中活著,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適應。到死時,不適應也適應了,不適應也無可奈何了,不適應也死了。
身處一種曠日持久的災難之中,為了與這災難拉開一個心理距離,可以有種種辦法。樂觀者會儘量「往前看」,把眼光投向雨過天晴的未來,看到災難的暫時性,而懷抱一種希望。悲觀者會儘量居高臨下「俯視」災難,把它放在人生虛無的大背景下來看,看破人間禍福的無謂,產生一種超脫的心境。
倘若我們既非樂觀的詩人,亦非悲觀的哲人,而只是得過且過的普通人,我們仍然可以、甚至必然有意無意地掉頭不看眼前的災難,儘量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尚存的歡樂上,哪怕是些極瑣碎的歡樂,只要我們還活著,任何災難都不能將這類歡樂徹底消滅。所有這些辦法,實質上都是逃避,而逃避常常是必要的。
如果我們驕傲得不肯逃避,或者沉重得不能逃避,怎麼辦呢?
剩下的唯一辦法是忍
我們終於發現,忍受不可忍受的災難是人類的命運。接著我們又發現,只要咬牙忍受,世上並無不可忍受的災難。
古人曾云:忍為眾妙之門。事實上,對於人生種種不可躲避的災禍和不可改變的苦難,除了忍,別無他法。忍也不是什麼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罷了。不忍又能怎樣?
所謂超脫,不過是尋找一種精神上的支撐,從而較能夠忍,並非不需要忍。一切透澈的哲學解說,都改變不了任何一個確鑿的災難事實。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並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苦仍然是苦,無論怎麼看透,身受時還是得忍。
當然,也有忍不了的時候,結果是肉體的崩潰—死亡,精神的崩潰—瘋狂,最糟則是人格的崩潰—從此委靡不振。
如果不想毀於災難,就只能忍。忍是一種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種自尊。
以從容平靜的態度忍受人生最悲慘的厄運,這是處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定理一:人是注定要忍受不可忍受的苦難的。由此推導出定理二:所以,世上沒有不可忍受的苦難。
對於人生的苦難,除了忍,別無他法。一切透徹的哲學解釋不能改變任何一個確鑿不移的災難事實。例如面對死亡,最好的哲學解釋也至多只能解除我們對於恐懼的恐懼, 而不能解除恐懼本身,因為這後一層恐懼屬於本能,我們只能帶著它接受宿命。
人生無非是等和忍的交替。有時是忍中有等,絕望中有期待。到了一無可等的時候, 最後就忍一忍,大不了是一死,就此徹底解脫。
我們不可能持之以恆地為一個預知的災難結局悲傷。悲傷如同別的情緒一樣,也會疲勞,也需要休息。
以旁觀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會想像他們無一日得安生,其實不然。因為只要想一想我們自己,誰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人生難免遭遇危機,能主動應對當然好,若不能,就忍受它,等待它過去吧!
身陷任何一種絕境,只要還活著,就必須把絕境也當作一種生活,接受它的一切痛苦,也不拒絕它仍然可能有的任何微小快樂。
身處絕境之中,最忌諱的是把絕境與正常生活進行對比,認為它不是生活,這樣會一天也忍受不下去。如果要作對比,乾脆放大尺度,把自己的苦難放到宇宙的天平上去秤一秤。面對宇宙,一個生命連同它的痛苦皆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計。
本文摘自《以智慧看人生,幸福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