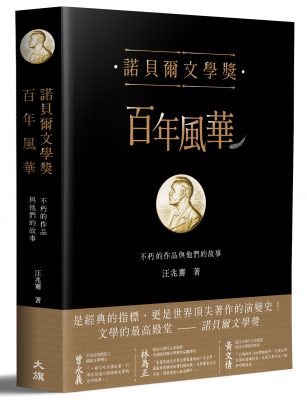人文史地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石黑一雄:我的雄心壯志就是要為它做出貢獻。
文/汪兆騫
2017年 諾貝爾文學獎110屆
石黑一雄
1954 —
日裔英國作家。
獲獎理由|憑藉充滿強烈情感的小說,揭示我們幻覺之下的深淵。
獲獎作品|《遠山淡影》、《浮世畫家》、《長日將盡》等小說。
瑞典文學院2017年10月5日宣佈,該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即將六十三歲的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理由是:「憑藉充滿強烈情感的小說,揭示我們幻覺之下的深淵。」
接聽瑞典文學院電話的時候,是下午一點,石黑一雄正在廚房,坐在餐桌前給友人寫郵件。接電話後,他並未在意,以為是假消息。因為他知道,自己在該屆諾獎中並非是熱門人物,博彩公司開出的諾貝爾獎賠率榜上,幾乎見不到自己的名字。當確定獲獎真實無誤,他又覺得如此高的榮耀砸在頭上有點荒唐。
當他平靜下來,回答媒體的採訪時,他說當下仍然有這麼多人關注一個嚴肅文學的獎項,實在令人驚喜。
擁有日本和英國雙重文化背景的石黑一雄,一直以「國際主義作家」自稱。他認為,自己雖被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但自己與另兩位魯西迪(Salman Rushdie)、奈波爾(V. S. Naipaul)不同,他們的小說總借用印度文學、宗教、歷史元素,完成對殖民主義的政治、文化批判,而自己是不以移民或民族認同作為小說題材的亞裔作家。不管世人怎樣試圖從他的小說中尋找出日本文化的淵源和神髓,或爬梳出英國文化的蛛絲馬跡,但石黑一雄本人從來不予認同。作為五歲便移民的石黑一雄,既沒有保留對日本故國的鄉愁,也沒有深深烙印大英文化,如果有,是作為移民在英倫成長中所遭受的冷遇和疏離的境遇。
石黑一雄雄心勃勃地說:
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日益國際化,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在過去,對於任何政治、商業、社會變革模式和文藝方面的問題,完全可以進行高水準的討論,而毋庸參照任何國際相關因素。然而,我們現在早已超越了這個歷史階段。如果小說能夠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進入下一個世紀,那是因為作家們已經成功地把它塑造成為令人信服的國際化文學載體。我的雄心壯志就是要為它做出貢獻。
讀石黑一雄的小說,就會發現,在他的小說世界中,其主旋律便是「帝國、階級、回憶,以及童真的永遠消失」。描繪出來,就是人一生下來,就被龐大的社會機器控制,情感被壓抑,甚至連人類的本能愛、性與夢想都被剝奪,文學藝術被權力污染,人性被毀滅,人類也走向滅亡的悲劇圖景。當然,石黑一雄同時又肯定世界還存在愛的力量,人類的罪惡都將得到救贖。記憶與遺忘、歷史與當下、幻想與現實、毀滅與涅盤、絕望和希望交織在一起。這就是瑞典文學院所稱,「憑藉充滿強烈情感的小說,揭示我們幻覺之下的深淵」,還稱石黑一雄是「一位偉大正直的作家」。
《遠山淡影》
處女作《遠山淡影》是石黑一雄1980年的畢業論文,於1982年出版,該小說講述在英格蘭生活的日本寡婦悅子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悅子隨第二任丈夫到英國定居,她有兩個女兒。其中完全日本血統那個女兒,因不理解英國文化,選擇自殺。悅子在處理其自殺善後事件時,陷入對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悠長回憶。小說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交叉飛躍中,呈現了一幅幅生活畫面。作者很少對這些片段的邏輯聯繫和事件發展做說明。一位評論家認為,《遠山淡影》中,「日本與英國的各種因素,被一張閃爍不定、隱而不見的意象之網籠罩著,被非常堅韌牢固的記憶的絲線牽連在一起。這是對於一位原子彈爆炸之後倖存者噩夢般的回憶,對於內心情緒騷動的極其冷靜含蓄的剖析」。《遠山淡影》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只有淡淡水墨畫般的意象,語言節制、隱抑、低調,令人印象深刻。《遠山淡影》一出版,石黑一雄便獲溫尼弗雷德.霍爾比紀念獎,又被文學雜誌《格蘭塔》評為英國最優秀的二十名青年作家之一。
《浮世畫家》
1986年,石黑一雄出版《浮世畫家》。同《遠山淡影》一樣,也是通過一位日本畫家回憶自己二戰從軍的經歷,意在探討日本國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是「一幅日本民族性的浮世繪」。小說的主人公是很有天賦的畫家小野增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接受軍國主義教育,認為發動侵略戰爭是一場保衛國家的聖戰。他以藝術宣揚軍國主義,在政府的推動下,他成了名噪一時的大畫家。然而,戰爭以日本戰敗結束。在美國的操辦下,日本推行「民族化」,人們開始對戰爭進行反思。小野增二在家庭、藝壇和政界的崇高地位蕩然無存,昔日的友人也棄他如敝屣,甚至連自己的愛女也以他的歷史為恥辱。小說中,小野增二陷入對過往的回憶中,反思自己的過錯和民族的前途。經過痛苦反思,過去的謊言被拆穿,小野增二認識到,原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整個日本民族是在為某種荒誕虛幻的理想獻身,而自己的藝術正是漂浮在這種虛幻的理想之中—「漂浮世界中的畫家」。
關於小說主人公小野增二,學界有多種解讀,有研究者認定他是一個慣於自欺的人,「具有將自己的願望和恐懼移位或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傾向,從而逃避面對自己的感情」;另有學者指出,小野增二有注重浮名、善於偽裝的虛浮偽善的一面。還有學者認為,小說中的小野增二,使讀者看到了「日本民族性特徵之一:投機性」,並不認同石黑一雄以「國際主義作家」自詡。
《浮世畫家》獲英國及愛爾蘭圖書協會頒發的惠特筆獎和英國著名的布克獎提名。同年,石黑一雄雙喜臨門,與洛娜.麥克杜格爾牽手走進婚姻殿堂。石黑一雄與麥克杜格爾,當年都曾是社會工作者,他們在諾丁山的西倫敦薩仁尼無家可歸者慈善團體的會議上相遇。當時石黑一雄是以住宅安置工作者的身份出席會議的。對這樁婚姻,石黑一雄非常珍惜,給予他文學創作最有力支持者,就是妻子。他說:「我和洛娜的感情是我最珍貴的財富,在我開始寫作之前,我們就認識了。當時,我們都是社會工作者,在倫敦一家慈善組織工作。那時,她把我當成落魄的歌手,憧憬著我們會一起變老,成為老社會工作者。然後我們可憐巴巴的,一起翻看《衛報》的廣告欄,找工作。」
《長日將盡》
1989年,石黑一雄創作的長篇小說《長日將盡》出版。小說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英國發生的故事,以給達林頓爵爺當管家的史蒂文斯之眼,見證了英國貴族的沒落。史蒂文斯忠於職守,將一生的才智和心血,服務於這位爵爺,看著主子在邪惡之路越陷越深的同時,自己放棄獨立思考和對權威盲從,最終自己也墮落,成為邪惡勢力的幫兇。
小說中史蒂文斯並非沒有自我懷疑,並非對達林頓的「事蹟」沒有懷疑,史蒂文斯回憶的不僅僅是人生之旅,也是對二戰時英國的榮光歲月的追憶,更是對自己靈魂的自我反省,力求自我救贖的過程。
《長日將盡》甫一出版,即榮獲當年的布克獎。同年,石黑一雄受日本基金會的邀請,使他離開日本近三十年,得以重回一直在思考和想像的故土。多年來,都是父母托人從日本購買教育資料,希望兒子能接受日本文化的影響。但在英語教育環境中,他只能保留下跟家人用日語交流的能力。他的日本之行,在日本媒體引起一場轟動。日本對石黑一雄來說,意味著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意味著印在腦海裡的故鄉的那些人和事,讓他想起自己與深愛的祖父朝夕相處的美好歲月。他曾感慨地說:「我意識到那是寄託我童年時代唯一的地方,而我再也不能返回那個特別的日本。」日本,對石黑一雄而言,只有記憶,再無鄉愁。
《無可慰藉》
1995年《無可慰藉》(又譯《無法安慰》)出版,這是石黑一雄的第四部長篇小說,也是最有爭議的作品。小說通過成年之後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力圖重構自己失落了的童年。小說主要講鋼琴大師賴德應邀來到歐洲一座城市演出。抵達之後,自己卻罹患失憶症,仿佛生活在夢境裡。他不認識的城市陌生人,卻仿佛是他童年時打過交道的人,且對他們的身世瞭若指掌。城市請他來,是希望振興該城,希望以他美妙的音樂淨化城裡人的靈魂,拯救已墮落的世界,而且認定他就是引導他們走向光明的領袖。一個失憶的音樂大師的舉止,自然讓人們大失所望,人們陷入漫漫長夜……,賴德並沒有為童年的創傷,找到安慰。
將夢境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編織在無意識的狀態裡,於是小說也成了一個冗長的、混亂的噩夢,但這不妨礙石黑一雄獲切爾特納姆文學藝術獎。
《我輩孤雛》
2000年,石黑一雄的第五部長篇小說《我輩孤雛》(又譯《上海孤兒》)問世。該長篇中,石黑一雄把目光轉向中國抗日戰爭前歌舞昇平的上海。英國人克里斯多夫.班斯克九歲時,其父母在上海神秘失蹤,他被送回英國。後來他從劍橋大學畢業,成為一名偵探,為了解開父母失蹤之謎,他重回上海。小說以記憶重尋的方式,追憶克里斯多夫.班斯克童年時代在上海租界生活,然而兒時記憶不再,雙親也不再,這場尋找雙親之旅,構成了一個失落在歷史敘述中的傷感的回憶故事。值得關注的是,小說中的主人公,在一種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租界殖民性語境中,面臨自我文化身份的喪失,成為文化上的孤兒。這是否是石黑一雄在為自我畫像呢?
《別讓我走》
2005年,石黑一雄的第六部長篇小說《別讓我走》出版。小說採用了科幻小說的寫作形式,將焦點設在一個時間、地點模糊的未來,再一次用回憶寫一個有關一座寄宿學校買賣人體器官,探討倫理與人性的脆弱真相的故事。小說再次入圍布克獎最後決選,同時獲世界文學獎獎金最高的「歐洲小說獎」。
《被埋葬的記憶》
2015年,睽違漫長十年之後,石黑一雄又推出自己的第七部長篇小說《被埋葬的記憶》(又譯《被埋葬的巨人》)。小說以英國不列顛人與撒克遜人交戰的年代為背景,講述了一對夫婦尋找兒子的回憶之旅。該羈旅穿越了層層疊疊的秘密,通過堆積的無休止的怨恨,試圖探問人類記憶、情感與愛的深遠博大意義。
閱讀石黑一雄的七部長篇,會發現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一直沉浸在回溯型的敘事結構中,一直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地追憶流光逝水般的往昔歲月,並在回憶時,對過往的人和事又都產生新的認識。對於移民作家石黑一雄來講,「回憶的過程蘊含了記憶,並且記憶伴隨著回憶」,它超越了個人回憶層面,還被寄予更深刻的集體記憶層面,民族記憶層面。不過,石黑一雄小說中的人物,既在回憶中追述自己的一生,也在追尋自己存在的文化記憶、身份記憶,以及那些隱藏在背後的歷史記憶。石黑一雄的回憶已進入審美經驗的一個途徑,在回憶中達到心靈的彼岸,在回憶中精神回歸家園。總之,石黑一雄的小說中,對回憶機制的描述,對回憶詩學的繼承,為讀者展開了一個「別樣的深邃而迷人的回憶的世界」。